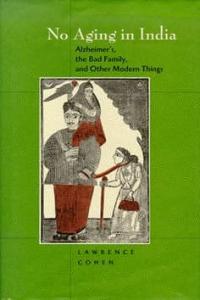
Lawrence Cohen, 2000, No Aging in India:Alzheimer's, The Bad Family, and Other Modern Thin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这是一本关于“老年”的书,却题为非老龄化(No Aging),着实让人称怪,却亦可成为读者阅读的意趣所在。文章虽篇幅冗长,然关注点始终如一:正如作者科恩(Lawrence Cohen)在前言所作的明示,“我以一个医学人类学家的身份,研究人们如何看待镶嵌于时间之中的身体与行为,从而理解老年这一概念。”在书的大部分章节中,科恩不遗余力地赘述着过程,即身体(body)、逻辑(reason)、声音(voice)及声音之内容被认为具备话语资格的能力,逐渐丧失、颓败的过程。此外,科恩有意识地区分了“Senility”与“Dementia”,相较于后者作为医学词汇直指个体病理学,前者所扩充的视角导向了以物质与社会过程各种互动关系所构成的等级。虽则提出了以上之双概念,却是重罗列而轻分野,科恩并不恭维人类学界曾盛极一时的二元主义(dualism),强调神经学说与个人化本土知识、家庭与老迈身体的政治经济不类于楚汉两界。科恩在研究时是尽心尽力的:他希望达到Geertz所说的深描,于是试图以质询的过程表达民族志深度而不停留于“田野”(the site)的进入程度;在不同规模上滚雪球抽样的同时,持续地扩展田野与质询方法直到详尽本文的核心议题。也正因此,文章有大量的细枝末节,又有不少重言迭叙,甚至于让科恩联想到了指称印度老人的“bakbak”(反复叙述的疯言疯语)。当然科恩骄傲地称之为民族志的乐趣与责任所在。本文的资料与写作围绕着两个广义的问题:一、“身体的年龄发挥影响的过程:身体的衰老被体验、命名、测量、对待并被纳入法律、历史和科学的过程是如何构建实践的?”二、“这些实践是如何因时间、空间及以民族、阶层和性别等为依据的各种人类区别而变化的?”
科恩的本次研究渊源于祖父;祖父与其畅谈的经历诸如衰老、记忆、医生、宗教、话语和工作是科恩迈入此领域的契机。同时又获得著名学府内的前辈、同僚和学生的支持,加之其十年间不辞辛劳地往返美国(波士顿、蒙特利尔、迈阿密)与印度(瓦纳拉西周边)或深或浅地遍访制度内外数千人,本文若非尽善尽美,也绝不失为上乘之作。然,科恩坦陈自己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位Nagwa贫民窟中一位妇人的问话:“您的写作能为我们做什么呢?”究其根本在于,此人类学文本偏批判而非应用;即便如此,科恩不喜印象中应用人类学近乎道德表演的行事,可是愿意欣赏其所具有的悲悯之情。他为剖析老年身体认识论而做出了不懈努力,谁人能说他执着的分析与详陈难现对于世界范围内人类同胞的细腻关怀?
印度暴动青年引发的社会动乱之恐慌,竟使得昙花一现的痴傻老妇形象与印度之神向苦难人世的传诏勾连起来,科恩难抑诧异:借助神学想象,凭空出现的老妇就能与因青年群体事件引发的政局安危理所当然地勾连起来么?这一现象中存在着的年龄、性别、政治便成为科恩文章的关键词,特别是嵌于时的身体何以描述印度正在发生的一切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为此,科恩首先驾轻就熟地从西方医学里找到了一个关于老年的词汇:Alzheimer's。曾有朋友疑惑地问科恩关于Alzheimer's究竟是疾病还是正常的衰老过程。科恩不置可否,但也坚信:西医的抽象不在普遍大众的理解能力之中,因而对于Alzheimer's这一新知,人们的理解完全借助大众媒体绘声绘色的诠释中那浅显的一部分,又因包括医药在内各种市场的商业化利益驱动,Alzheimer's某一方面的特质被夸大地劈入受众的意识中,形成一种缺乏变通的刻板印象,成为老年群体须避之而又易得之的有妄之灾。出于此,科恩用同情的笔触写到倘使真正的Alzheimer's会逐渐剥夺老年人的自我感,那么又有多少痛苦的老年人是因社会建构之蛮力而非这种生理性的诱因被剥夺了自我的呢?这是现代性身体的悲哀之处。但印度的情况在作者考察时又有所不同,Alzheimer's作为现代性的知识没有占据社会意识的主流,于是印度老年身体的现代性悲哀被一些学者笼统地归咎于联合家庭的解体。科恩希望透过当地人的原声(voice)验证对印度现代性身体悲哀的理解框架,同时也掺杂了地方、全球经济实践和文化在个人直面自我和世界时起到的结构性功能的考察,以求真切地逼近印度社会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情境。当科恩泛舟行于恒河之上,看着一条条通往城市的石阶随行而过,望着那些佝偻老人沐浴恒河,这种流于视觉表层的异乡之景与暂时远离却内蕴其中的宗教、旅游、卫生、学校之间交杂的关系,使Cohen时刻警醒着对浮世绘似的文化以浅尝辄止的解读,并决心不能陷入旁观者式的绮丽想象之中。
在1988年萨格勒布(Zagreb)典礼上,趁此聚会的全球人类学者为“老年痴呆”(Dementia)以及相关Alzheimer's之涵义展开了一场争论,西方显见的词汇于印度本土学者而言晦暗莫名。争论倒让科恩有了一次重审西方老年学的机会,顿悟:西方对老年病理的认识存在于孤立而特定的个人疾病过程,而印度对老年人病态的解释植根于家庭动力学和文化危机之中。面对同样的衰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认知视角:欧美人视个人为自主有界的实体,自我存在于个体化的独体躯体中;印度人则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实践和体验自身,不断通过相连而互赖性的自我与其他的身体分享及交流。因而前者的衰老更个体化绝对化,而后者的衰老更社会化相对化。因此,科恩边缘dementia而用senility的目的就是不让自己被欧美的视角支配,且充分体现出研究所在地瓦纳拉西中个人身体与生活的社会构建。Cohen所说的衰老(Senility)需要三个身体的支撑:衰老的身体(参与者为自己);被指认衰老的身体(参与者为社会他人);作为集体衰老表征的身体(参与者为世界)。这在之后成了本书叙事的分类方式。
在寻找受访者的过程中,科恩非常注意避免导师凯博文(Kleiman)所说的归类谬误(category fallacy):印度内部老年人口比例远远少于欧美社会,且医疗资本的匮乏使得当地老年人的就诊意识薄弱,一方面加剧了他以dementia为标准寻找研究对象的难度,另一方面促使他遵循凯博文教导摒弃先验的西方医学视角,没有因找不到诊断为dementia的老病人而气馁,而是以senility为标准成功寻找到最佳的对象。
至于主要研究地,恒河边上的瓦纳拉西对于科恩来说是一块研究老年的妙地,老妇来到这里度过晚年的最后光景,并最终火化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各类老年信仰者居于此,其中古鲁信徒(sannyasis)的人生四阶段说令科恩对这种老年新视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在这里,科恩(1)用两年时间对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中老人与其家庭进行了调查(2)走访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如休养所、寡妇之家、政府的庇护所、慈善机构、当地的支持网络等,(3)还探查了当地制度和从业者,包括印度草药、招魂者、社会法庭以及政治宗教协会的研究等。科恩事后回想这次研究,承认瓦纳拉西作为一个田野有其特定性,然他自信所写的内容却是超越了地方而能与全球对话的。
纵观此文,笔者再一次从人类学文本中读到了隐喻作为线索理解社会事实的重要性。如科恩发现印度语境中,狗低于其他动物,是连施舍也不该高攀的存在。而印度老男人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大方地把六十岁至八十岁以后的自己比作狗,无不表现出年龄之增长带来失去家庭权力后的失落和自贱之情。而其笔下与狗为伴的Mashima老人默默地昭示着印度老人的窘迫。迈入老年被比作第二次童年,老人却没有因此享受孩童得到的珍视,而是被框定为只懂哭闹叫食而无用功的废人。科恩屡次提及被孩童嘲笑欺凌的老妇人形象,实质上影射着印度老人与孩童结构上的对立,而老人总是沦为次等的地位。面对有限的资源,家庭更愿意将之节省在孩童身上,而不愿意赠予老人,这时候,老人再度被边缘化为家庭的他者,尤其是老妇便成了疯婆子。另外,孤寡老妇人又蒙女巫之喻的污名,而成了吊诡的存在。借由对狗、第二童年、女巫譬喻的剖析,印度老人之亲历便栩栩如生了。笔者希望自己在未来书写人类学文本之时,能够将视角转移到中国人对话与思维中隐匿的习以为常的隐喻,以之作为文本创新的起点。
此外,笔者对于老年之话题颇有些感触。恰如科恩所指出的,不管个人是否能够活到年龄意义上的老年,我们始终守着老年的包袱在度日。现代资本社会对年轻、强壮身体的渴求日益将老人边缘化。这个社会功利主义地想,老人的用处是什么呢?当知识不再需要代际传承,职业精英建构起了阶级壁垒,老人成了他者,陌生甚至带点恐怖。我们极力避免老年的各种特质,进行记忆进补、美容、健身,当我们的能量消耗在自我身体的塑造后,当我们结果发现老年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时,我们的人生就成了荒诞的闹剧。科恩提醒我们,人对不老的追求并非枉然,当他发现有老人用无年龄的视角看待自我和他人时,那么老人是不老的。当我们不把身的老化看成心智的老化,就可能获得一份悠然自得。当然了,人老心不老有赖于生活史的演变发展,作为他人生活情境的组成者,我们是否有能力为老人的不老做些什么,也为自己的不老埋下伏笔?科恩最担心的是老人被异化的情境。当老人被用来标榜孝道,而非获得真正的关心;当某一种老年疾病的名义被用来推卸赡养不当的责任;当他者作为救世主出现以妄自尊大的姿态用偏误的方式干涉我方的老人生活;我们是否该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Dulari是Cohen遇到的一位可怜的无助“疯”老妇,她在失去死去表亲的经济资助后不得不在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之家度过死亡前的最后阶段,她的“bakbak”没有接受对象,她的声音陷入无限的虚无。科恩的接触告诉我们,Dulari之类的老人需要的不过是倾听罢了。倘若任何人类社会能时刻反省文化的力量是否像印度宗教一样被阶级强权利用着制造涅槃幻梦,期许顶着正义的旗号谋求私利,那么“bakbak”就会骤减,亦能免于许多弱势自我催眠着成为共谋。
复旦大学2011级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冯锦锦 推介